
对他,我心里有几分崇拜。为至今已罕见的中国文人的狷介和狷狂。
他是一条汉子。高大笔直,形象就给人宁折不弯之感。
我与他相识有年头了,但几次都是公干,皆为了撰写瓷都景德镇的电视专题片。记得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的秋季,在他的古陶瓷研究所里。研究所藏匿于闹市中,幽清宁谧,是幢建于明代成化年间的商人的住宅,这本身就是一页历史。匾额题为《品陶斋》,雅。
在明代成化民居中,品陶斋的学者们正专注探研复修成化瓷,时光仿佛倒流,明灿灿的阳光流泻在已逝岁月的小径上,他的话语或重或轻地叩动着瓷文明古老的门扉……
他的谈话很文学,且富哲理,让我惊慕不已。他说:木会朽、石会崩,人会亡,而,瓷,历经岁月的淘洗,却依然固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时代的光辉。后来由江西电视台拍成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获得1990年中国电视二等奖。如果说解说词中有闪光的东西的话,那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他在中国古陶瓷和陶瓷史研究上独树一帜,为国人更为外国人刮目相看;他研究切入的视角把握的细微论述的深刻是一般陶瓷学者无出其右的。但是,他却是个半路出家的行家里手,他学的是中文。
1962年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分配到景德镇陶瓷学院讲授文艺理论。这仿佛是历史的刻意安排,这所全世界唯二的陶瓷学院(还有一所是英国皇家陶瓷学院)就位于湖田古窑遗址附近。湖田,没有湖,却有田,有水草淤塞日渐干涸的古河道。田野寂寥、旷野疏阔,几座硕大的古窑包悄然无语,昔日的河道孤寂呜咽,何处寻觅昨日“村村陶火延、处处窑火”的踪影遗痕?可这硬是湖田古民窑遗址!方圆四十多万平方米。始于晚唐五代,兴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和元,衰于明代,七百余年窑火熊熊不熄,而今荒寂了。那时,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的古瓷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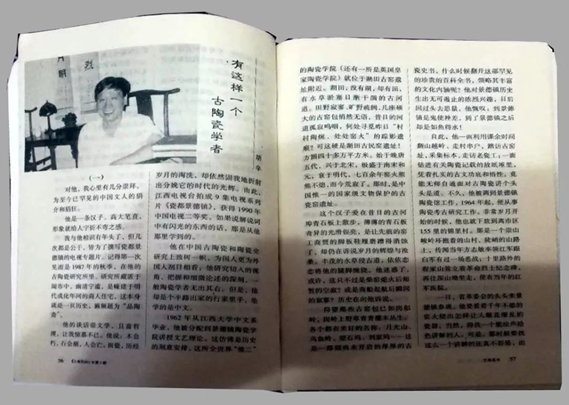
这个汉子爱在昔日的古河埠青石板上散步,薄薄的青石板奇异地光滑锃亮,是让先前的窑工商贾的脚板鞋履磨蹭得消蚀了,却仍在诉说岁月的辉煌与沧桑。丰茂的水草侵古道,依依恋恋将他的腿脚缠绕。他迷惑了,或许,这只不过是柴窑熄火后短暂的空寂?或是商船起航后瞬间的寥廓?历史在向他诉说。
仰望那些古窑包已如岗似岭,岗岭上野草青青灌木丛生。各个都有美好的名称:月光山、乌鱼岭、望石坞、刘家坞。这是一部部尚未开启的厚厚的古瓷史书,什么时候翻开这部罕见的珍贵的百科全书,领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呢?他对景德镇历史生出无可扼止的浓烈兴趣,日后回过头去思,他慨叹:到景德镇是鬼使神差,到了景德镇之后却是如鱼得水!
自此,他一面利用课余时间翻山越岭、走村串户,踏访古窑址、采集标本,走访老瓷工;一面钻进有关陶瓷记载的故纸堆里,凭着扎实的古文功底和悟性,他无师自通竟能面对古陶瓷讲个头头是道。不久,他被调到景德镇陶瓷馆工作,1964年起,便从事陶瓷考古研究工作。可很快非常岁月开始,他也就下放到离市区一百五十五里的锦里村。那是一崇山峻岭环抱着的山村,陡峭的山路上,传闻当年方志敏率领红军跟白军有过一场恶战;十里路外的程家山耸立着革命烈士纪念碑,再往深山坳里走,便有当年的红军医院。抗战岁月,日本鬼子打到了景德镇的外围,但没能进来,说是景德镇为名副其实的山城,山路上的伏击让鬼子闻风丧胆。他说,他的爷爷当年亲手打过日本鬼子!在锦里时,他迷上了拳术,有说是柔和的太极拳,有说是激昂的少林拳,反正已有点小名气,似确有英雄之后的血脉。
一日,省革委会的头来景德镇参观,他要看看千年不熄的窑火烧出怎样让人眼花缭乱的瓷器,当然,得找一个能绘声绘色讲解的人。可是,那时候要找这么一个讲解的还真不容易,出身不好的不行,出身好成了反动学术或技术权威的也不行,根正苗红但不懂古陶瓷、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还是不行。情急间,有人一拍脑门,说,就是他——
他就从锦里用军用吉普给接到市里。在又高又胖的紧绷军衣的头面前,他高大笔直的身子也不知道得稍弯弯,头的脸就往下耷拉,他视而不见,自顾自侃侃而谈。头眉头一皱,找碴,就是一口咬定没听明白。学文的他岂能没感觉?其时正在解说一件珍贵的百极碎瓷,百极碎,又名碎纹釉、碎瓷、碎器。是釉面布有纹片的瓷器。这本是烧制工艺上的缺陷,即胎与釉的膨胀系数相差过大而出现的一种裂纹。但古代的制瓷者就智慧地利用这一缺陷来作装饰瓷器的特殊手段。他见头将脑壳摇得像个拔浪鼓,知是刁难他,一眼见着头的上衣有粒扣子从扣眼绷出来了,即不动声色说,好,我打个比喻,譬如一个大胖子,他硬要穿件号数小了点的衣服,一经大运动或心气不平,嘣——衣服就得脱线开缝了!围着头的众人已忍俊不禁,却又胆战心惊,把头惹恼了,怎么办?头的脸也憋得血红,可他,面不改色心不跳照讲不误,还要加一句,比方还不够确切,不知听懂了没有?头这时缓过气来,似笑非笑答曰:你这小鬼头。众人都为他捏一把汗。可谁知不久他就从锦里调回市里,让他继续研究古陶瓷。也许,头是故作姿态以显示胸怀开阔?也许头毕竟是带兵上过战场的,他这份临危不惧的从容拨动了那根久已麻木的神经,他才逢险化夷。
(二)
他只对古陶瓷心存感激。他忘情陶瓷考古。他的家,不过陋室一间,整个空间都让破瓷器乃至一堆堆碎瓷片给占据了,挨墙立着书架,古籍书刊堆满其间,没一本他没看过,不看的书上不了他这书架。他还从乡间朋友那借到了或从焚烧中抢救下来的宗谱,这能作陶瓷考古的背景或旁证资料。他自个儿则席地而卧,来了朋友,还真找不着立锥之地!即便这般杂乱,朋友们还是很愿在这斗室里听他侃陶瓷,他的侃,有理论有实践,有史料有考据,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有引人入胜的文学味,还有让你不得不与之共鸣的激情,哪怕你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陶瓷门外汉!
直到他下“逐客令”,你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逼仄的小天地。景德镇是驰名中外、历史悠久的瓷都,历代古窑遗址星罗棋布,地下文物极其丰富。十年动乱中,他就这样,从湖田窑遗址走向一个个古窑遗址,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考察了两千多个自然村,采集瓷瓦片标本,寻找历史的踪迹。常是数月在外“流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像是个“乌须子”,这是景德镇的人喊叫花子。“乌须子”讨的就是中国古陶瓷的秘密。他很乐天,从不作痛苦状,秋冬季节,是最好的田野考察时期,也是一年忙到头的农民稍稍的闲淡时节,他一路交朋友,也不仅仅是眼里只有瓷,他喜跟老表们一块拉二胡、练武功、寻草药,算是苦中作乐。回到城里,瓷厂里的坯坊佬是他的朋友,学院的年轻教师是他的话友,老学究亦是他的忘年交!他要进了图书馆,自家也就成了个老学究,有回钻进北京图书馆,一呆也是几个月!他说:写一篇论文,不知要看多少资料,研究多少实物,厚积薄发才见份量。
他也真是个好样的,1974年,他第一篇陶瓷考古论文就在国家级杂志《考古》上发表。题名为《宋元芒口瓷器与复烧工艺的初步研究》。作者用自己的眼光去探寻宋元时代支圈组合式的复烧窑具的重大作用,同时,从点点滴滴枝枝节节的考证入手,将古代名窑定窑的烧装技术及定窑对景德镇的影响和关系论断,读来饶有趣味又令人拍案叫绝。这篇论文切入视角的突破、材料的丰富翔实、论证的精到得无暇可击,还有漂亮的文学语言,真的叫人耳目一新!论文一出手便占领了制高点,很快就被日、英、美等六国翻译转载,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日本专家发表评论说:“中国新进的充满朝气的学者刘新园氏研究宋代的独特的效率很高的窑具的论文很值得日本研究者学习,如果我们满足于过去的那些知识将会感到羞愧。”
接下来就是国际陶瓷学会邀请他出国访问。那时节可不是后来的出国成风成热成河的情状,那时节出国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外国人邀请你,仿佛意味着接下来就是你不回国,也不好说是叛国。于是有关领导难以决断且谆谆告诫他,他捺不住,即作拍案而起状,慷慨陈词的却是:你以为我算老几?!我的名字如果脱离了景德镇,一文不值!他感谢这方水土!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太轻描淡写了。应是血浓于水的至情: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朝朝暮暮在一起,生生死死不分离!
他挚爱这方水土,可是他并不是这方水土的土著,连赣人都不是。他是湘人。籍贯湖南澧县。在他身上,那股刚烈勇猛、宁折不弯,似又应了“湘人不死,华厦不倾”之语。
之后,他所发表的几乎每一篇论文都很快就在国外广为传播。1983年,仅日本《陶说》杂志就连续八期登载他的论文。他出名了!他的名字的确是与景德镇连在一起,不可分离,相映增辉。
他的论文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影响最大。蒋祈所作《陶记》,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系统地叙述当时景德镇瓷业情况的专著,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元代著作。但是,他却在研究中发现疑窦,从蒋祈对制瓷技术、市场销售的记述,从对书中税制、职官等的考证,与宋元两代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比较,论断《陶记》是南宋嘉定七年至端平元年之间的作品。这一创见正如日本专家所言——是“晴天霹雳”,震撼了国内外学术界。因为这论证将《陶记》的写作时间提前了一百多年,这部世界陶瓷史的重要文献诞生年代的更正改写了中国陶瓷史!诚然,这篇论文还“是我国科技研究中之力作”。无怪乎日本《陶说》慨叹:“刘氏论文以众多的资料为基础来研究陶瓷史,又远远超过陶瓷史,它的广度就像读社会科学史。”
(三)
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学者。1982年市政工程处在珠山铺设地下电缆线,当推土机沉闷地刨过地表时,他恰恰路过。一条宽约12--30公分的全是瓷片的地层掠过眼帘,他的眼睁大了:不是垃圾,也不是景德镇处处可见的渣饼堆,是干干净净的碎瓷片!他的眼晴发亮了,他高叫:不准推!要推就从我身上推过去!奇迹出现了。清理发掘出的是大量的宣德御窑瓷片和叠压在下的永乐官窑瓷片!又在中华路口市政府南围墙前发现一座宣德窑炉遗址。被岁月埋葬的历史终与火热的现实结轨,与活生生的生命相撞了。自元代始就在本土设立的珠山御窑,确切的窑址就在这里。景德镇的古陶瓷史和古陶瓷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再引起世界的瞩目。
他带领工作助手,在已对全市城乡300多处古窑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考查工作的基础上,一面配合城乡基本建设,一面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清理,使大量珍贵的地下文物免遭破坏。这以后的十几年间共抢救历代地下古瓷(残器)达30余吨!并组织人员进行了细致的修复工作,已修复的陶瓷文物达1200多件,大部分都是罕见的陶瓷珍品,有一部分是海内绝品,不仅为国家创造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财富,亦弘扬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此同时,他还对景德镇城乡130多栋明清古建筑进行了调查,使之得到就地或集中保护。
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最可贵处是他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从多学科的角度切入,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研究古陶瓷。比如说,面对发现的古窑遗址及出土瓷,如何考证它们的相对年代、当年是怎样烧炼的、瓷的器型纹饰的来龙去脉、是皇家瓷出口瓷民用瓷等等,不能不涉及考古学、硅酸盐化学、陶瓷工艺学、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学、经济学、中外文化交流史……融会贯通方能柳暗花明风光无限。正是:全史在胸、血脉贯通。
他斩钉截铁认为出土瓷的研究当然比孤独的传世瓷可靠得多。有尊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侧永乐前期地层中出土的青花冲耳三足大鼎,满绘汹涌又宁静的海之潮水纹,当有纪念出海之意。北京故宫藏有相同的传世祭品,说是宣德年间的,他说,显然有误。

我读过他的一些论文,如若我对陶瓷的性灵有所感悟的话,离不开他的文章的启迪。譬如:景德镇的御窑究竟创建于何时?他一言以蔽之:《元史·百官志·将作院》记载得清楚翔实:忽必烈在灭宋之后的第二年至元十九年,便在景德镇设置了唯一的为皇家生产瓷器并兼造棕、藤、马尾笠帽的官窑浮梁瓷局,瓷局长官称大使为正九资品,掌管官匠八十余户。引经据典,不容置疑。又如:对成化瓷上竟有“明宣德年制”款的现象,他的解释别出心裁又在情理之中。他说:郑和六次出使"西洋"带去的货物,最受欢迎的是景德镇青花瓷,带回来的对中国陶瓷影响最大的则是苏泥麻和胭脂石;苏泥麻是青花瓷色料,胭脂石是祭红釉色料之一。成化年间已无进口青料,而成化瓷深受宣德瓷的影响,以至出现在成化瓷上竟有“明宣德年制”款,并非假冒欺诈,而是“恨不同时”的向往。——真是文人的满怀情感的理解和解释。
对多才多艺的宣德帝,他亦看到宣德帝的另一面:走不出骄奢淫逸!绘画、田猎、奕棋见其情趣高雅,斗蟋蟀却足见他的荒唐奢靡。宣德官窑出土物中以蟋蟀罐最为丰富,其中造型秀雅、纹饰丰富的想是宣德帝亲自使用的斗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宣德蟋蟀罐在社会上极其罕见,是因为斗蟋蟀时情绪太激昂而毁之?他反复推敲曰:非也,36岁的宣德帝驾崩后,是皇太后和维护正统者为维护皇帝形象而销毁之故也。这,当是胸有成竹的史学家的一家之言!
深厚的文学功底,始终不泯灭的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力,还有永远的人文情怀,是他在研究中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又别开生面的动力之一。
中外陶瓷考古专家、历史学家专程来景德镇参观考察的,络绎不绝,一致公认品陶斋为中外景德镇陶瓷考古中心。他接待的国外学者数以千计,并牵头组织了国际古陶瓷学术交流会;又走出去,在港澳和国外举办中国陶瓷艺术展,扩大了中国瓷都景德镇的对外影响,让古老的中国陶瓷文化大放异彩。
著名的英国古陶瓷学家约翰·艾惕思便是他的好朋友。艾惕思原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后辞去此职任教于牛津大学。艾惕思对中国古陶瓷史情有独钟,曾几次来到景德镇踏访。我去到瑶里、高岭时,山民皆知道这个外国老头。
艾惕思对他,可说赏识又信赖。曾写信给他,饶有兴趣追问:“元王朝为什么要把唯一的瓷局设置在景德镇呢?龙泉窑不是当时生产规模最大、技艺水平最高的窑场么?是影青瓷美还是卵白瓷美?元代印有‘太禧’与‘枢府’的官瓷为什么只是卵白的呢?元青花上流行的六瓣花是什么花?......”视角独特且细致入微,也许应了“旁观者清”?他则感叹:提出这些问题比解决这些问题更有价值,其难度更大。
我想,将艾惕思所提问题一一解答出来,便是景德镇之所以为景德镇的魅力所在。
艾惕思询问的“六瓣花”,有学者考证为射干;而他认为就是开在山里田头老百姓喜爱的山桅子花,艾惕思欣然同意。1983年古稀老人去世,他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他自信地说,写得很好。我拜读后,亦被感动。特别是结尾处——幻想有一天在艾惕思爵士长眠的墓地上,献上一束山栀子——我的眼睛濡湿了,冰冷的瓷使他的情感更纯更炽。
1997年中秋,在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栏目中,他与台湾的古陶瓷学者一块出场,他蛮动情地说:我们修复古瓷就是要让它们团圆。
真情已将陶瓷和文学浑然一体。
像他这么一个个性极强的学者汉子,按世俗的眼光,是很难与人相处的,非常高兴的是,他有不少好朋友,还有一个和和美美的家庭!
1998年深秋,我又应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一记者之邀,再次去景德镇干纪录片撰稿的活,我在景德镇呆的十天中,他先是外出,归家后又不慎跌断了小腿骨,而且,又即将应德国之邀,去作讲学,当然,不见客。可我还是找着他的同事,想见见他,他竟应允了。于是,我去到他的闹中取静的家园,很雅。小院里满是绿意。他的两层小楼,楼上书房很清淡,有几幅货真价实的古字画,还有明式桌椅,日本的纸灯罩、法国的台灯与中国风的古色古香亦相得益彰。那次交谈十分融洽,他诚挚希望央视能好好宣传宣传景德镇。
这以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一资深编辑从我处得知有这么一个古陶瓷学者后,油然而生敬意,说,此人真值得好好宣传。想让我较正规地采访他一次,写篇专访,可是,却很难联系上他,他那时应东南亚几个国家之邀,正作巡回讲学;后来,好不容易我和他都在北京且电话联系上了,可他即乘飞机去西欧讲学!他说:欢迎你再来景德镇长谈。可是,在报刊上宣传,如果是十年前,那倒也罢;可我现在老了,只须实实在在地做点事了。我觉得心里格登一下,像被人冷不丁往心湖里掷进一块石头!我从未想过他也会老!他也会退休!他老了么?即使老了,他也是海明威笔下的《乞里马扎罗的雪》中的主人公。他是这样的男人。
他的中国古陶瓷情结,他与景德镇的不解之缘,让我难以释怀。他却说,他毕竟最衷情的是文学,可一辈子走过来,说古陶瓷是他的衣食父母也罢,说是相濡以沫的患难妻子也罢,文学却始终是他的一个梦,是挥之不去的梦中情人!
他的名字——刘新园。
胡辛,原名胡清,中国作家。1945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黄山太平。现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景德镇市荣誉市民。1983年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一发不可收,涉小说、传记、影视文学、散文随笔和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至今已出版书四十本。其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数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等出访美国、马来西亚、捷克、埃及等。三部传记在海峡两岸出版,在世界华人区中有较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以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创造了真诚、鲜活的人间情致和灵活不拘的艺术表达形式。
(作者:胡辛,发表于《人物》2001年第3期)